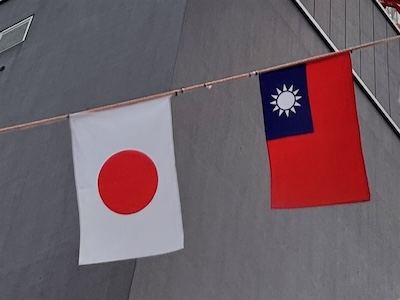自己的歷史 自己解釋
作者 / 韓非
歷史只是歷史解釋,所謂歷史只是以歷史的事件作為平台,所作歷史的解釋而已。因此英國歷史有所謂輝格黨的歷史解釋;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幾乎整個十九世紀的法國都在爭論王權派、共和派、或社會主義派的歷史觀點:例如說,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如何解釋?即使最喜歡找尋共識的日本也有所謂薩長(薩摩藩、長州藩 )對明治維新的歷史解釋。再看歷史最平順的美國,近年來每次大選都有所謂紅軍州、藍軍州之別,南北區域間楚河漢界。事實上,是因為對內戰歷史的解釋不同衍生相異的政治態度,文化上,誰說南北戰爭已經結束!?

今年,剛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持續四載的戰爭殺戮數百萬一代歐洲精英,改變人類文明和歷史事件的原因,當然也有不同歷史的解釋。有些歷史學家說是德國中了英國奸計(德國擴充大海軍,參與非洲殖民地爭奪及柏林—巴格達鐵路計劃都威脅大英帝國利益);也更有歷史學家認為奧國的王儲在塞拉耶佛 (Sarajevo) 被刺只該是嚴重外交事件,假如俄皇尼古拉不以斯拉夫民族解放者自居,支持塞爾維亞 (Serbia) 全面動員俄國軍隊,局勢也不會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可以俄皇震怒說為例,繼續我們的歷史討論,如果俄皇尼古拉不熱燥暴怒,可能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凡爾賽條約中,處理誰來承繼德國在華利益的山東問題,沒有山東問題,也不會有五四學生的愛國運動。又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德國政府的特務也不會在戰爭末期,偷偷地把流亡在歐洲的列寧走私運回俄國,就不會有布爾雪維克的十月革命,就不會有「共產國際」,也不會有鮑羅廷和蘇俄在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也不會審視時勢,想趕上世界潮流而接受革命先進國家的經驗和奧援來國共合作。俄國人穿列寧裝,我們穿中山裝,軍營中他們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他們有赤卡(Cheka),我們有軍統;他們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這一切好像我們已趕上世界最新的潮流,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愉悅地說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千古名言!
因此,假若俄皇尼古拉不暴怒,中國現代歷史會不會不一樣?是好是壞?是福是禍?
——本文想表達倒不是歷史的虛無論,而是歷史的偶然論。歷史都有偶然和任意的成份,在天平任一方加上一絲稻草,天平就會傾斜。說過去發生一定是唯一的、必然的、是偉大的、恥辱的,都是缺乏想像能力的結果。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軍事家估算希特勒若多兩年的準備,戰爭的結果就很難預料。德國V-2飛彈早一年上場,諾曼地登陸是幾乎不可能。發現原子核會分裂是德國的物理學家,而且德國也有與愛因斯坦同等級的偉大物理學家海森柏格(W. Heisenberg )。海氏在政治上有法西斯的傾向,卻沒有向德國當局進言發展核子武器,這些事例當時一定被視為不是那麼重要,但若偶然地被發現受到重視,及早執行,對歷史結果的衝擊是很難估算。
我們可再以西安事變作為另一事例,假若沒有西安事變,或是即使有西安事變,但假如史達林不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對日本抗戰而消滅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威脅,而不全力相救,蔣委員長可能就被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公審而處決,那麼中國的現代史又要重寫。
西安事變的結局,蔣氏「攘外必先安內」的軍略完全破滅,在救國家、救民族號召下全力抵抗日本軍閥,蠶食華北,建立第二滿州國的企圖,不再像「何梅協定」、「冀察政委會」時採取的綏靖妥協策略。蘆溝橋事變日軍踩了西安事變後新的紅線,區域性的衝突演變成全面對抗,兩敗俱傷。史達林的戰略成功了,毛澤東說:「全中國解放要感謝日本軍閥」。
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甚至是荒謬的成份,為了有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及更靈敏的歷史感受,一種替代性 (alternative) 的歷史看法是必要的。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會怎麼樣?假如俄國革命不成功(它的成功有其僥倖的成份)又會怎樣?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會怎樣?假如1939年五月發生在外蒙的諾門罕戰役,日本關東軍能擊敗蘇聯紅軍,日本陸軍必然沿西伯利亞鐵路到貝加爾湖,尋找戰略的油源,而不依賴海軍所提南下印尼、婆羅洲和英、美、荷衝突,那麼太平洋戰爭不會發生,甚至蘇聯感受到東線的壓力,史達林會不會不敢和希特勒簽訂密約,瓜分波蘭,引發英法對德宣戰,希特勒會不會多二、三年的準備?
西方世界從啟蒙時代開始,都有個進步 (progress) 的觀念,大部份十九世紀代表進步的力量是自由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獨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左派社會主義,卅年代最進步的蘇維埃政權卻被證明是最極權和反動的。那麼「什麼是進步的內涵?誰代表真正進步的力量?」都需要解釋。歷史是歷史解釋出來的。「偶然」需視為「必然」,是理性的發展進步的力量,假若能完成控制宣傳的工具,可以令整個國家民族發狂,讓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個具體而微的偉大領袖!
那麼過去真正的歷史是什麼?事實上,沒有真正的歷史,歷史是根據新的一代人解釋而出現的。假如新一代人不想解釋它,放棄自己的解釋權力,只有命中注定地接受不相干的過去人所創作,所解釋的歷史,而受其控制。因為人的文化和歷史是有結構的,這個結構多少控制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若我們不願思索新的歷史解釋,對舊有的結構有所批評,甚至畏怯創作自己的歷史,我們只有配合生存在那結構中,絕對沒有哲學家柏格森 (H. Bergson) 所說「文明躍升」的能力。
幸運地,今日工藝技術的進步,沒有一家一姓,一個政黨和政府能控制全民的思考。偶然發生的,或是偶然發生而被撲滅,或是被壓抑而一時沒有發生的;人類全面的歷史,而不是某民族的歷史;都可以是我們創作歷史的元素,我們有選擇的權力。我們可選擇對我們相干的,對我們有意義的歷史,歷史的結論不在過去,歷史的結論在未來。
我們無需對過去歷史負責,我們需對未來歷史負責,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歷史自己創作,自己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