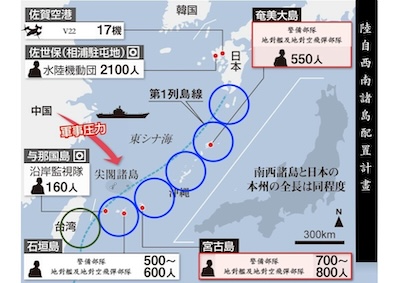「人一輩子都這麼難熬嗎?還是只有童年這麼苦?」
「一輩子都這麼難熬。」
–盧貝松,「終極追殺令」
最近看了一部描述中下階級的年輕人生活與戀愛的日劇,看起來似乎與一般我們想像中的偶像劇完全無關,但是卻讓筆者看得感慨萬千。
「那一年我們談的那場戀愛」是部少見的日劇:男女主角都年少失怙,被人收養。只有高中學歷的他們離開鄉下或小城市,來到東京這個大城市,做著繁重的體力工作:在搬家公司當搬家工人的男主角,老人照護機構工作的女主角。他們的工作加班無盡,有時連續日夜值班好幾天,工作了數年也不會加薪;甚至在日本公司放棄終身雇用制,大量使用聘僱人員時,他們的工作總是岌岌可危,隨時都有可能被裁員。睡眠不足、聚餐時得挑選最便宜的餐點;即使這樣,女主角也仍然有夢想:但是與其他的青年勵志日劇不一樣的是,劇中幾年來一直穿著同一件夾克的女主角的夢想,不是當上首席舞者、名設計師、或是進入大商社出人頭地,而只是「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睡在自己的床上,有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如此卑微的希望。
 圖片來源: 宅宅新聞
圖片來源: 宅宅新聞
這樣的男孩女孩們還是渴望感情,渴望溫暖;但就連他們的愛情也是一樣的平實卑微:1997年時,木村拓哉與松隆子主演的日劇「戀愛世代」中,男女主角間感情的重要象徵物,是一顆所費不貲,也沒有實用價值的水晶蘋果。但是2016年播出的「那一年我們談的那場戀愛」中,男女主角的定情物,卻是一罐白桃罐頭;那是兩人第一次相遇時,男主角從搬運貨箱中拿出來,送給準備逃離家裡為了脫離貧窮,替她安排的婚姻的女主角。甚至就連男女主角劇中唯有兩次的親吻,都是發生在兩人於便宜的家庭餐廳用餐後,男主角的貨車中。這,看起來像不像我們周遭,那些在飲料店便利超商機車行與小工廠裡工作的年輕人?
充滿了這些平凡不過的小細節,與一股鬱悶壓抑氣氛的這齣日劇,不只是對一般仍然光鮮亮麗,激勵人心,有些脫離現實的偶像日劇之反思,其實也是對於日本現實的殘酷描述;而這樣的描述,似乎和我們周遭的生活越來越相似。台灣的年輕人們也得忍受著低薪、長時間的勞動;我們的人口高齡化越來越嚴重,青壯年人除了工作外常常還得兩頭燒,負起照顧長輩的責任。越來越多的人只求溫飽,沒有作夢的心思,也自認失去了作夢的權利。
在這樣一個22K與貧富差距巨大的時代,也難怪許多人喪失了戰鬥意志,屈就於越來越忙碌,薪水卻越來越少的生活;這不只是日本台灣社會獨有的問題;之前經濟學人曾報導過,世界各國犯罪率不見得減少,但是全球青少年犯罪率與吸毒比率大致上卻都年年走低。當然這也許可以說是犯罪防治上的成功,但是我們如果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青少年們是否連鋌而走險以改變自己現況的意願,都已經失去?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高唱理想,宣稱努力就能出頭天,但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在現代做著低階的勞力服務工作出頭天的機會,益發不可能。在劇中,另一個持續出現的鏡頭是突破了柏油路面,矗立在寒風中的小花。這也可以看做是對於日本年輕人們突破困境的期盼。與逆來順受的日本青年不一樣的是,近幾年來台灣風起雲湧,由學生與年輕世代主導的抗爭運動與大規模抗議,可說是這群台灣年輕人為了打破現有社會死水般的壓迫氛圍,起身反抗的做為;當一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僵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覺得看不到未來,他們怎能不起身反抗?而這同時也獲得了社會大規模的迴響。;正因他們不願再忍受毫無出路,溫水煮青蛙的生活,才會在時事的刺激觸發下,起身反抗吃人社會的不公不義,或是上街大遊行,或是佔據公家機關。
這部日劇的劇作家,當年因寫出「東京愛情故事」這齣名日劇一炮而紅。而在漫畫家柴門文「東京愛情故事」的原著漫畫中,有一幕是由故鄉來到東京工作的男主角在荒唐的一夜後,看著朝陽,告訴差點發生一夜情,同樣也是由鄉下來到東京工作的女性:「雖然東京的麵淡而無味,居然還有一堆人在吃,讓我很驚訝;但是看到這樣的朝陽,就讓人燃起再繼續在東京打拼的希望。」。但是到了2016年的「那一年我們談的那場戀愛」,男女主角最後卻決定一起回到北海道去照顧女主角的養母。在台灣,也有許多人對這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感到失望,決定回到故鄉奮鬥。但不管是起身反抗,遠走他國或回到故鄉,能夠做出變化的都還是有資源的中產階級子弟們。如何讓那些只能夢想獲得一份工作或一個棲身之地的孩子們,能夠有更好的生活,實踐更大的夢想,將是新政府與青年世代未來重要的努力課題。否則,盧貝松的電影裡,那段受家暴的小女孩與住在隔壁的殺手之間的對話,就會是我們青年世代無法醒來的惡夢。
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