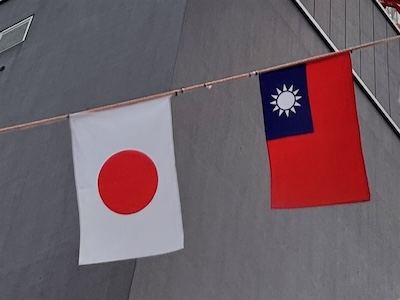對30歲、在中學擔任通識科老師多年的田方澤來說,這個盛夏之後的開學是他最難熬的一年,「我們不可能以為還可以正常開學、正常生活,香港不一樣了,我的學生不一樣了。」
9月2日,全港500多所中學(相當台灣國中與高中,共6年)的開學日之前,許多老師失了眠。他們之中,有的像田方澤一樣,在過去近3個月,白天遊行裡不時遇見反修例的學生,夜晚則透過Telegram與Instagram,時時發訊提醒學生們注意安全;有的老師甚至親自帶著受傷的學生前往私立醫院就醫、動手術 ,避免學生被警察檢控;而有的則會接到學生們夜晚捎來心情沮喪的短訊,適時接住學生情緒的創傷。

從學生、老師到校長,這騷動之夏對身心的挑戰強度與廣度,是前所未見的。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的程度雖然不一,卻是遍地開花,從6月分一直延燒到9月2日的開學日,全港500多所中學就有100多所學校的學生發起罷課,相當於每5所就有1所。
原本香港政府預測,這場學生大幅參與的反送中運動將在開學之際逐漸淡去,但眼見集會遊行、罷工罷市、癱瘓交通等的抗議活動方興未艾,香港教育局罕見地在8月20日向所有中小學緊急下令。教育局長楊潤雄臨時召見各校校長們,向全港中小學發布「做好準備迎接新學年」的指引,表示「教育局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罷課」;而指引裡多次提及「任何人士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更不應煽動或鼓勵尚未完成中小學教育的學生在具爭議及正在發展的政治事件上表態或參與有關行動,亦不應以學生的參與作為壯大聲勢、施壓的手段」。
但是,不少準備返校上課的中學生們,一時半刻心思還回不到課業。他們在社群媒體上成立「各校關注小組」,討論如何返校後罷課、是在校內或校外罷課、是一週罷一天還是罷課不罷學、是共同罷還是各自罷⋯⋯“be water”的策略思考一樣漫進中學生的課堂,縈繞在師生的心頭。
有的學生把教室門口裝設成連儂牆,學校裡即便提及與反修例無關的議題,學生們所思所想也會連結到催淚瓦斯、布袋彈、黑警、政治制度、香港未來⋯⋯。
「老師,如果香港徹底變成中國,我努力讀書要幹嘛?」
田方澤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讀書時就搞過社運,2014年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是他當時的老師,他一直關注社會,目前還擔任香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香港教協的副會長。但儘管這些年經歷多次運動,當了快10年高中老師的他,這回卻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開學,該怎麼教那些被城市巷戰洗禮過的學生。
雖然中學生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9月分,也曾有過為期一到數天的罷課,但當時的罷課在佔中開始不久就展開,且時間相當短;不像這次,反送中運動累積了3個月巨大的能量。這個暑假,學生捎給老師們的問題愈來愈棘手而不易三言兩語回答,像是:
老師,在自由社會使用武力是否合理(不論警察和示威者)?
老師,雙方以「公義」之名訴諸武力、升高衝突,那還算是公義嗎?
老師,香港的未來會怎樣?運動的未來會怎樣?我們該怎麼辦?
老師,你怎麼看學生罷課?老師是否不應該有政治立場?
老師,你告訴我,以後要怎麼相信警察?
老師,該如何與「藍絲」父母相處?
而更沉重的,是學生問老師:如果香港以後徹底變成中國,我努力讀書要幹嘛?
田方澤說,「有些很好很乖很會念書的學生(中學六年級)明年就考文憑考大學,他們也有疑問。我很苦惱的是,當老師總要散布希望啊,那現實是有沒有希望?政府說不要談政治可能嗎?」
上街頭就是上課
對不少中學生而言,這次的運動是個在短短3個月間跨度很大的「密集課程」——反修例教給他們通識、歷史、化學、護理、法律、國際政治,更考驗他們的體能與情商。
面對每個週末遊行街頭的緊張,在前線擔任救護員、17歲的Daniel說,「我不能崩潰,如果我挺不住這些壓力,我就沒辦法救人。我就沒辦法完成我的責任。」原本應該是享受青春校園時光的Daniel在這兩個多月經過了街頭衝突的洗禮,他學會了對他人付出以及自我負責。
Daniel在他小六的年紀就遇到了雨傘革命,當時懞懂的他從電視上看到許多14、15歲的中學生衝撞立法會,慢慢地意識到香港是一個有問題的社會,「原來有這麼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他自此開始關心社會發展。
Daniel就讀的中學位於港島,這間中學的學長在2014年雨傘革命時曾經成功罷課,雖然學長已離校,但是事蹟仍流傳下來。Daniel在反送中運動於6月進入大規模示威的階段時,跟幾位同學在學校網站上發起連署簽名,要求政府撤銷《逃犯條例》修正案。Daniel說他們在這間規模只有300、400人的學校,短短幾天就蒐集到上百個簽名,「學長們都跑回來簽。」
Daniel的中學所在地有不少來自福建的移民,校內的學生家長多數都是支持政府的,也支持修改《逃犯條例》。訓導主任要求學生不要到網站上連署,甚至多次約談Daniel,讓他備感壓力。但這些沒有讓他停止。現在是學生會長參選人的他,與幾位同學一起與校方交涉,希望在9月2日開學日進行「罷課不罷學」活動,開學後,每個星期一在校內舉辦罷課,其他時間正常上課,但校方並沒有給出正面回應。
像Daniel這樣的中學生以及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成為反送中運動的主力。香港中大教授李立峯6月曾在幾次反送中行動現場做簡單的民調,初略看到6月9日遊行,30歲以下青年佔所有參與者的44.5%(其中22歲或以下佔26.3%),6月16日這數字到57%(其中22歲或以下佔30.8%),而6月21日,參與包圍警總的群眾更有91.7%是青年(22歲或以下佔63.9%)。李立峯曾描繪這群年輕人,「對社運沒有太多負面情緒。對雨傘運動有好感,對社運內鬥沒有感覺。愈年輕愈沒有帶著以往的舊恨進入反送中運動。」
運動者年齡不斷下探
青年裡有30歲上下的社工、護士、律師等專業工作者,也有20歲出頭的大學生,但和雨傘運動相比,中學生的面孔在6月分後大幅增加。
這些原本在喝喜茶、玩手機遊戲《王者榮耀》或《PUBG》(台譯《絕地求生》)、看中國抖音、下課去補習或party room的13、14歲少年少女,離開自己的小世界走出來。香港社會都在問,反抗運動的年齡層為何下探?
長年關注香港年輕人處境的太平紳士黃英琦,身為教育工作者及社會創新者,也是一所中學的校監,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表示,「坦白說,我還在理解的過程裡。我年紀比較大了,但我跟年輕人談得來,我理解的是,前線有不少學生來自中產家庭,覺得香港社會有很大的不公義,也有些中學生覺得自己生於亂世,有責任出來。甚至也有些新移民二代來港多年,他們覺得香港要保持現在這樣,自由是很重要的。也許你問小孩子,自由是什麼?他們不一定說得清楚,但他們會說,過了深圳河就沒有自由。
我從不少年輕人的故事裡看見普遍性吧。他們不是想要香港的獨立,而是要尊嚴、要自由、要參與,他們要共同創造,是有這樣的情懷在裡面⋯⋯但政府不願答應任何訴求,甚至誤讀訴求(註),讓最近的氣氛非常緊張。」
除了認為政府不公義、香港失去原有的自由和法治、一國兩制的制度崩毀外,也有人認為,過去10年間,通識科教育以及升學考試制度的變革,也是影響香港中學生的遠因。
過去兩週,中國境內不斷有人送出各式帖子和論點,把年輕示威者的出現歸因於香港在中學推動通識教育。這種論調在2012年「學民思潮」的年輕學子引領反國教行動之時,就已經出現過了。甚至前任特首董建華近日還自承犯錯,在他任內搞出了通識科,讓學生出了問題。
但2009年擔任通識科科目委員會主席的趙永佳,卻不認同這種保守論調。他日前在《明報》寫了篇通識教育的始末,提到他在2015年和香港中央政策組開展了「90後青年的大型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訪問了25間中學、2,896名中學五年級的學生,「是次調查,說明了未有證據顯示通識科教育令學生變得狹隘和偏頗。相反,通識科當中的『明辨性思考』令同學們能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來檢視議題,而非只從自身利益和立場出發。一個例子是喜歡通識科的學生,較認同新移民及雙非兒童應享有與其他香港人同等的機遇和福利。數據並未有顯示學生因為通識科而變得本土化,或是排斥內地移民。通識科要認的『罪』,可能就是成功執行了賦予該科的公民教育任務,令一代年輕人更關注了社會事務。」
憂鬱少年的轉變
另一個則是升學考試制度的變化。黃英琦指出,過去8到10年,香港的教育制度改變,從兩個高考變成一個高考,每年每次高考有5萬多名的青年人,不論你擅長的是什麼,都要考同一個試。但香港政府能補貼的大學只有16%,表示只有1萬多的學生能進大學,進港大的只有頭3千名的拔尖學子。這讓升學變得非常高壓,孩子被逼得非常緊,學生是不高興的。而且憂鬱的學生,從她接觸到的學生觀察,比例從10%到20%增加到現在的30%。
我們或許無法估算總共有多少中學生走上街頭,但他們對反修例的態度,在過去半年內,從冷漠、注意到熱切關注,轉變是相當顯明的,甚至在夜晚與警方對峙的場子裡,不難看見中學生年紀的孩子站在前線,或在中線協助物資,或當救護員。是什麼激發出他們的反抗意識?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學副校長說:「我常說,如果學生那麼容易教成我們想要的樣子,我們教書就不會那麼辛苦了。通識教育是給他們多一點思考和討論,但學生的行動力是另一層來的。我覺得是網路上的影響。」
這位副校長說,「他們在學校,無聊地滑手機、打遊戲,在學校沒有什麼行動。有些本來有憂鬱症的學生,嚴重到沒辦法上課的這一種,但在這次,早睡早起地去街頭上,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他們本來困在家裡,很多問題解決不了,覺得那是自己的問題,但他們後來發現,原來不只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制度出現問題,他們就跑到街上面,原來可以跟群體有solidarity的關係。」
不管是為了對抗中國因素、追求自由法治、反對警方暴力、抗議港府無視人民,每個抗爭者站出來的理由儘管不一,但相同的是,連登(如同台灣的PTT)、Telegram這類的網路平台,成為把他們彼此動員和相互連結的工具。
次文化外溢:「巴絲打」的情誼與歸屬感
在我們訪談的中學老師和前線運動者身上,的確觀察到年輕人將許多屬於他們世代的次文化元素外溢到此次的運動。
在與警察對峙的街戰裡,不難看到電玩世界裡的次文化元素。
例如在《PUGB》這款手遊裡,每個遊戲者乘降落傘到遊戲陣地裡,與軍團裡的人共同對抗敵人,在過程中,遊戲者每隔幾秒鐘會撿起地上的物資,有煙霧彈、槍砲、安全帽、防彈衣、急救包等,這稱為「食雞式」的補給。幾名不具名的受訪護士和社工告訴我們,這與運動過程彼此補給或現場投遞物資是很像的。
香港年輕的紀錄片導演廖潔雯,跟上前線記錄了此次運動,她的短片《手足》,某種程度說明了香港年輕世代的價值。在be water、無大台、戴起口罩不識誰是誰的無臉孔抗爭裡,當夜晚他們要離開,前線的人會向巷弄裡頭探喊:「各位手足,我們要走了。前線還有沒有人?要走了,不然會落單。」
「手足」的說法在香港網路文化裡已多年,手足用來稱呼成員。在連登或Telegram的群組,成員們的「巴打」意為brother,「絲打」是sister,「巴絲打」是brother and sister。前線運動者如18歲的鍾翰林,他的Telegram有個群組上寫著「12巴絲打」,是他們最核心討論運動策略的12人。
樸素的金屬框眼鏡與青澀的舉止,藏不了鍾翰林的青春,但眼神中的憂鬱和不疾不徐的言談又讓他顯得早熟。經過了香港這幾年的社會運動,他本來是一個喜歡在家中打電動看書的宅男,如今勤上前線。170公分左右的他53公斤,不久前才在旺角被疑似挺政府的人士追打。在社運中活躍而小有名氣的他,早已是挺政府派的眼中釘。
鍾翰林拿出手機秀給我們看8月29號在網路上流傳的檔案,這份有如通緝名單的資料裡,鍾翰林的頭像與親人的詳細資訊全部大剌剌地被公開。這裡面,有些親人的資料,連鍾翰林都不知道,像是他父親與繼母結婚的時間,以及他遺忘很久的過去老家的電話。鍾翰林的隨身背包裡,是他深藍色的香港護照,隨時有買機票逃亡的心理狀態。談到上街衝撞可能付出的成本,他說:「我不想死、我不想被抓,但我已經有了準備。」
有如此深刻的體悟,是因為他在街頭上,找到了他想做的事。「什麼是真普選?對我們來說,只有香港獨立才有真普選。就算香港50年不變,只要中共不喜歡我們,就會把我們辛苦爭取的民主收回來。」鍾翰林也在過去3年間從溫和派走向了勇武派,在運動中找到歸屬,「我們稱手足,指的是別人是我們的手腳,我們是很密的。」鍾翰林自己沒有兄弟姊妹,在他看來,「現在跟我出去運動的巴絲打,比我跟我跟家人親密。」
累而不倦,持續串聯
為了與巴絲打齊上齊落,過去3個月和鍾翰林一樣進入運動中的年輕人睡眠很少。他們把自己的零用錢省下來坐不便宜的香港地鐵,有遊行示威的前一天,他們夜晚到處蒐集物資。沒有示威的時候則要畫文宣圖、寫文章,如今則要幫助其他中學的關注組罷課,組織串聯,讓示威的力量更大。
反送中運動這幾個月來刺鼻的催淚瓦斯與警棍盾牌敲打的噪音,取代了暑假的蟬鳴聲與歡笑,多數受訪的學生對這場運動的結果並不樂觀,也不認為政府會讓步,他們都說自己好累了。
他們雖累但不倦,打起精神在連登和Telegram上彼此打氣。站上前線感覺挫折的人會天真地在連登上說,自己很小,還有很多事想做,其實想試試喝酒什麼感覺,想交女朋友;也有些巴絲打說有友伴想輕生,而後頭的巴打絲打們甚至會開玩笑留言「大不了我的胸給他摸」,還引來許多人按讚。
這種既青春又在短時間成為大人上前線的矛盾,並存在這次運動裡。他們稱自己「連登仔」,他們說「一個人都不能少」,大喊「香港人加油」。
儘管帶著面具,但有具體而清楚的「對手」和任務,讓這些手足們彼此照應。
「我的一位學生,全年都沒見過她笑,但她在街頭上跟隊友一起時,我見到她笑,」這位副校長觀察,原本學生在求學和生活裡沒有感覺到太多的希望,但當他們在街頭上的經歷後,跟其他人建立了很多人際的關係,找到平常沒有的東西。「以前是一個人,問題都是自己的,現在有人可以一起解決問題,甚至懂得負責,因為在前線就算掉個包都很可能害到別人讓警察找上,反而他們比以前更有責任感,」她說。
歷經城市巷戰洗禮的一代,已經不同
3個月的運動,中學生與大學生們彷彿一夕長大,老師、學校、家長與社會要怎麼面對這群生命體驗和智識都已不同的學生們呢?
由於香港主要中小學幾乎受政府的資助與監督,有不少老師和校長表示,這次的壓力比佔中時候大很多,時間很長,對學生影響大,教育局出台的文件與信件,也不讓學生搞集會,不支持學生罷課。
黃英琦的想法是,這個夏天結束後,學校老師不可能天真地撇過頭去,更不可能輕鬆在開學上課時問:「你們夏天過得怎麼樣?」她說,學校勢必得更包容,讓學生可以有傾訴和被關心的空間,希望不同意見能彼此溝通,不要有欺凌。
黃英琦不去想未來是不是悲觀 ,但她看到香港年輕人從6月分至今展現的多元面貌:「有創意一面,有激進的一面,有堅定的一面,很衝動的一面,和很國際化的一面。他們在6月與8月兩次登報,讓世界各國都關心香港,這完全不是聽人指使,不是被操縱。不單是我還有我的朋友們,都非常驚訝。但近兩星期,運動的暴力升級,警方大規模搜捕,難道這場運動不能有更好的結局?」
面對未來,不論抱持的是理智的悲觀主義或意志的樂觀主義,這一代都已不一樣。這樣長大的中學生,承受的衝擊比傘運時的學生更大,怎麼化解可能的傷痕?他們雖保有理想主義卻也目睹更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暴力和被濫用的權力,這一代成長的人,會建造出怎麼樣的香港?對這個城市有什麼想像?
走過這個充滿騷動的盛夏,不管香港社會怎麼回應這群走過煙幕與巷戰的年輕人,他們都不一樣了,這不再只是一兩位領袖的變化,而是一整個世代香港人的轉化。
作者 / 《報導者》李雪莉 楊智強 (原文出處:報導者)
註:報導者實習記者許家瑜對此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