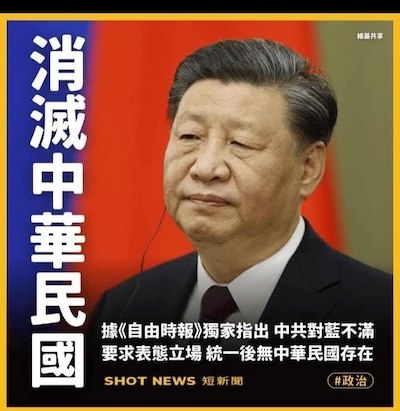2024年立法院新會期啟動後,「國會擴權法案」風波迅速點燃社會怒火。藍白兩黨以人數優勢強行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法,引發民眾對程序正義、權力分立及民主價值的深層焦慮。隨即,從民間自發發起的「青鳥行動」到「反國會擴權大遊行」,社會對立已臻高度對立態勢,網路、造勢場合常看到不同支持人馬互相謾罵、宛如狹路見仇人。藍白陣營習慣宣傳成綠營及其外圍組織所為,事實上,若非去年藍白挾國會過半之傲,試圖宰制行政權,致政府機能癱瘓影響人民權益,方有被民意反撲的結果,故大罷免不僅是對政黨行為的集體表態,更成為對台灣民主制度健康程度的壓力測試。

罷免制度是現代民主體制中重要的一環,其意義在於當民選代表背離民意或濫權時,民眾可透過合法程序撤回授權。台灣自實施《選罷法》以來,罷免案多為個案進行,直到2020年後「罷韓」、「罷黃捷」等案例讓罷免成為具有群眾動員與政治操作性的工具。2025年的「大罷免」是首次以「國會行為」為主訴求的大規模聯合罷免,這顯示台灣民眾對於立法權濫用的警覺正逐漸提高,也反映社會對代議政治信任逐漸流失。
制度設計上,台灣的罷免門檻相對高:需25%選區合格選民同意,且投票率需達一定比例。這代表罷免難以被濫用,必須有充分民意支持,方能成立。因此,將「大罷免」視為「民主暴民化」未免誇大其詞,反之,它是一場民意強力反制權力濫用的制度性回應。
筆者認為,對國會議員行使罷免權是官逼民反,官台灣憲政制度,行政權及立法權皆有直接民主性,然長期以來國會成為畸形發展,常有情緒性、利益交換性立法,更甚者,從實務來看。選舉代價太高,急需選後其他方面補償,無論是利是名,皆註定立委行使職權無法客觀中立。此次罷免潮的核心,是民眾對藍白聯手強推《國會職權行使法》修法的反感。該法案將立院調查權、藐視國會罪制度化,但程序未經充分討論、公聽會匆促草率、質詢紀錄缺乏透明,引發「立法霸權」、「搶奪行政調查功能」等質疑。
社會之所以出現「青鳥行動」這類非政黨主導的抗議潮,是因為制度原應保障人民參與與監督的功能失靈,而人們只能回到最原始、最具象的民主工具:投票與罷免。這是一種制度危機下的群體免疫機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股罷免動能來自各地方志工與年輕世代主導的草根運動。他們不受政黨操控,發動募資、聯署與連署,透過社群媒體散播資訊,彌補主流媒體不報導的空白,構成一場「去中心化的公民行動」。
支持藍白者質疑罷免制度被「濫用」、導致國會失能,甚至呼籲修法提高罷免門檻,以阻止「選舉結果未滿即翻案」。但從制度層面來看,罷免並非否定選舉結果,而是對「當選後失職」的糾正機制。
若立委無視選區民意、違背競選承諾,甚至違憲立法,那麼民眾以罷免表達不信任,是憲政制度中重要的權力制衡。制度不該成為護航政治人物的防火牆,而應保障選民主體性。反過來看,若制度讓民意無法有效懲戒濫權,那才是真正危險。
作者 / 劍藏鋒

![[轉]【賴怡忠專欄|美中注意力內轉,台灣應加速國防革新 – 思想坦克|Voicettank】 ](https://newcongress.tw/wp-content/uploads/2026/01/思想坦克-Voicettank.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