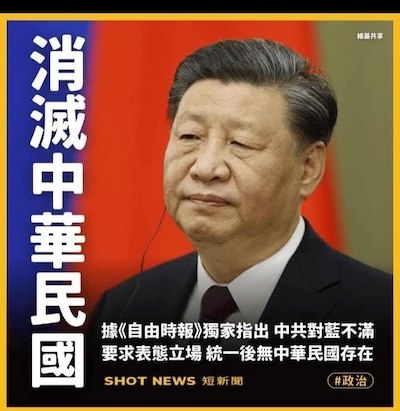7月18日,立法院通過《刑法》修正案,針對兒童遭受虐待致死或重傷等情節,新增多項加重處罰的條文,並大幅提高最低刑度。這項修法普遍被視為對剴剴案的直接回應。然而,這種以個案為起點、情緒為推力的立法模式,正是所謂「現象立法」(Event-driven Legislation)的典型,也再次凸顯出台灣在兒虐預防與制度治理上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困境。
本次修法不僅揭示社會防護網的脆弱,更反映出台灣對於公共危機的應對往往倉促──刑度設計的比例失衡、程序未經深思熟慮、立法目的與手段不成對應,導致一場以懲罰為主軸的象徵式行動。在輿論壓力與政治回應的交互運作下,我們倉皇補漏,卻未同步關照問題的根源,結果反而使法律的體系更破碎、社會的節奏更紊亂。與其說這次修法止住了流血,不如說它只是將悲劇包裝成一紙制度的回應,卻沒有回到那個早已被忽視的問題現場。

實際上,所有犯罪都源於多重因素交錯影響,虐童亦不例外。造成兒童遭受長期虐待甚至致死的,不僅是個別行為人的惡意,更是家庭結構、社會連結與制度監測多重斷裂所共同促成的後果。彭淑華教授在〈兒虐致死危險因子與防治策略之研究〉中指出,兒虐致死的風險因素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兒童層面,包括年齡幼小、依附性高與表達能力不足;其二,家庭層面,包括單親結構、親職能力不足、家庭暴力經驗的延續與經濟困境;其三,制度與社區層面,包括社會支持薄弱、跨系統通報不全與高風險家庭難以持續追蹤等;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使施虐行為往往不是預謀的惡意行動,而是長期生活壓力與孤立處境中缺乏紓解與介入的結果。
然而,這次修法卻幾乎忽略了上述風險層次的任何一環。法條所關注的,僅是刑度的提高與象徵性的威嚇,卻未碰觸制度性修補的迫切需要。現行兒少保護機制依然存在大量斷點與真空:社政與醫療體系之間的資訊斷裂、學校與社區網絡的介入不足,尤其是在高風險家庭跨區移動時,既有的通報與追蹤資料難以即時銜接,讓孩子反覆暴露於隱形風險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許多施虐案件並非第一次出現危機訊號,而是每一次訊號都未被妥善處理,才終於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
當我們僅僅寄望於重罰嚇阻、懲罰昭示時,其實是在以懲治取代治理、以情緒替代制度。結果往往不僅無助於犯罪預防,還可能讓法制更加扭曲。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兒童受虐致死的風險,來自於守護失能、家庭破裂與社會控制機制鬆動三者的交錯──犯罪行為並非孤立的道德墮落,而是結構壓力缺乏出口時的劇烈爆發。因此,若不能及早辨識風險、建立穩定的制度支撐與社會干預網絡,即使再重的刑罰,也只能對結果發威,卻永遠無法修補過程中的斷點。
如果司法是最後的防線,那麼第一線應當是預防性的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該問的不是「怎麼懲罰得更重」而是「怎麼能讓下一次悲劇不要再發生」,但是卻向吸食毒品一般一再貪戀嚴刑峻法;我們清楚知道,這是建立完善而有效的預防性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是一條長長長路,但是我們得走,這才是我們面對剴剴案最踏實的回應。
作者:李正穎

![[轉]【賴怡忠專欄|美中注意力內轉,台灣應加速國防革新 – 思想坦克|Voicettank】 ](https://newcongress.tw/wp-content/uploads/2026/01/思想坦克-Voicettank.png)